互联网新闻信息许可证服务编号:61120190002
陕西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29-63907152
2025-05-26 14:46:20 来源:阳光网-阳光报
■季风/文字整理 黄朴/供图

主持人: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主编、作家)
对话嘉宾:黄朴(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报刊社社长、作家)王淼(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黄朴。
嘉宾简介
黄朴,陕西丹凤县人。编审、中国作协会员、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陕西“百优计划”作家。现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报刊社社长。
在《人民文学》《当代》《江南》《中国作家》《钟山》《青年文学》《大家》《芳草》《山花》等刊物发表大量小说。
曾获路遥青年文学奖、陕西省年度优秀作品奖、第五届柳青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
王淼,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华人文学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国青年作家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黄河》等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研究论文、文学评论数篇。

作家黄朴。

在第五届柳青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贾平凹向获奖作家黄朴表示祝贺。
王淼:近年来,您出版了长篇小说《如我》(2024)、小说集《丫丫的城》(2022)、《新生》(2019),政论随笔集《向着幸福前进》(2011)等,并荣获路遥青年文学奖、陕西省年度优秀作品奖、第五届柳青文学奖等文学奖项。作为一名出色的作家,您是如何与文学结缘的?如何开启您的写作人生的?
黄朴:谈及文学的萌芽或种子,那也许要追溯到少年岁月。秦岭南坡绵延不绝的群山、夏日争奇斗艳的花朵、鸟的唱鸣、虫子的欢腾、河水在门前不舍昼夜地奔流,这一切都构成了文学原初的氛围。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鬼怪土匪故事、秦腔花鼓等民间戏曲、丧事中吟唱的凄凉哀婉的孝歌、剪纸及其他各种民间艺术都对我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投稿、退稿、发表的循环,塑造了我愈挫愈勇的写作性格。写作对我而言,既是打开平行世界的钥匙,也是对抗虚无的途径。尽管未获广泛认可,但能在虚构中体味创作的神秘与生命的辽阔,已是莫大幸事。
王淼:您的作品常呈现一种由乡入城的叙事动程。具体地说,您倾向于将人、物放置于“动态的语境”中加以透视。其中,您所塑造的“入城”姿态,并非从容的、心向往之的,而是焦灼的、痛苦的,甚至是“逃离”的,这是您的“设计”吗?
黄朴:当下时代已经呈现了高强度的流动、迁徙、奔赴、交融,多重因素交织融合,社会呈现出极端繁复的样态。流动与融合已经成为时代的核心,而最显著的莫过于由乡村向着城市的流动。我塑造的“入城”姿态其实是多样化的,有从容的、主动的、心向往之的,有被迫的、焦灼的、痛苦的,甚至是逃离的,这绝非我的主观“设计”所致。我只是忠实于自己的观察与体验,尽力呈现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由乡入城的新一代农村青年的心灵嬗变、灵肉纠葛,去理解他们的奋斗、梦想、纠葛与歌哭,去呈现他们灵魂深处的脉动,而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路径上,他们由乡入城或由城返乡的故事会越来越精彩,值得每一个作家去关注、描绘。
王淼:作为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个体,您拥有丰富的、真实的“城——乡”二元生命体验。您是否有意将其征用为新的创作资源,尝试以一种“居间”的状态,转型“新乡土叙事”“新城市叙事”,或是其他?
黄朴:我庆幸自己既有农村生活体验,又有着多年的城市生活经验。乡土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谱系中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曾涌现出诸多彪炳文学史的作家和作品。他们对某个阶段、某个时期的中国乡土社会皆做了精彩的叙写,创造了诸多经典形象。当下的农村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上。我目前写作的着眼点是关注中国乡土社会的转型、变迁,即由传统乡土文学向着新乡土文学叙事的转变,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同时,吸收融合其他创作方法,力图在人物塑造、叙事方法和文本结构方面有新的突破。城镇化在加快,城乡在融合,社会在急剧变化,人的身份更具多重性,很难用单一的题材确定作家的写作疆域。“新乡土叙事”“新城市叙事”或者其他以地方命名的概念,只是一种批评、阐释、标识的需要,我不会自我限定,而要力图不断拓展自己的写作疆界,不断突破自身的局限,使自己的写作与时代有着某种彼此映照,呈现出丰富、多样、细腻、敏锐等质地。
王淼:您的小说有一种黏稠、湿漉漉的质地,带给读者一种缓慢的、有温度的,甚至温柔的窒息感。这是一种充满着矛盾、甚至悖论的叙事效果。我们暂且将之称为“雨林质感”。读者进入文本后,如走入雨林一般,稍有不慎就会因热气致病,甚至致命。您对此怎么看?
黄朴:小说是生活的映像。读者读出了某种滋味,自然有其道理所在。能与“理想读者”产生共鸣、共情,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真是幸莫大焉。正如一千个读者的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解读,这也许正是小说艺术的魅力所在。我小说的底色大抵是灰色的、阴郁的,调子是低沉的,但文本背后透着向上的追问和亮光。它不是那种扑面而来的热闹和喧嚣,不是表面的花团锦簇。它伤惋、低沉、宽阔、细腻、敏感,甚或如你所说的有“温柔的窒息感”。我生于商洛,那里的风土人情自然有别于关中和陕北,雨季绵长、植被茂盛、雾气弥漫、鸟兽横行,自然呈现一种黏稠、湿漉漉的质地,呈现某种类似南方雨林的气象。
王淼:您的小说不断窥探着世界的边界、苦难的边界、人性的边界,甚至无限试探“向下”的限度。有学者将之称为“向下美学”。您对此怎么看?您为什么要不断“向下”?
黄朴:感谢你的发现归纳和总结。我只是尽力贴着人写,贴着物写,在想象与虚构中,自身幻化为小说中具体的人或物,体验他们的情感潋滟、喜怒哀乐,我就是他们,他们就是我,努力拓展表达的边界,尽力呈现自己的洞察与想象,力图使小说文本更具丰富性、开放性、象征性、探索性。
我还是借用西北大学教授陈然兴的评论更为准确。他指出,积极的“向下认同”的心灵姿态不仅构成了黄朴小说底层叙事的着力点,同时也构成了黄朴小说艺术结构的原则。作者是如此信任、同情、亲近他笔下的人物,以至于他敢于、乐于用人物意识来替代自己的外位意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他作为作者的审美主动性,他的主动性恰恰表现在,用一种“求同”而非“求异”的思维来观照人物,从而形成一种艺术上的、积极的“向下认同”。
王淼:您的写作处于纠结与挣扎中。荒诞、讽刺,甚至暴力,与“新生”“幸福”“前进”形成了剧烈的对比。您对此怎么看?此外,您的小说集《新生》与但丁的《新生》同名,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巧妙的必然?
黄朴:我的写作始终处于纠结与挣扎的矛盾纠葛中。荒诞、讽刺、阴郁,与“新生”“幸福”“前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它是小说多面性的呈现,是对现实的发现和勘探,也是对温暖、亮光、向上力量的追求。致敬经典是创作者的宿命,但丁以《新生》书写灵魂的觉醒,我则以女性视角呈现进城者的精神蜕变——“新生”既是逃离土地的阵痛,亦是重构自我的契机。
王淼:作家贾平凹曾称赞您:“善于体察世相人心之幽微,以洞彻现实的亮光。”您之所以能够在小说中透视驳杂的世道人心,是否与您丰富的新闻从业经历有关?抑或是其他?
黄朴:新闻教会我用显微镜观察社会肌理,文学则赋予我望远镜般的想象力。新闻结束的地方,恰是文学升腾之地,新闻忽略的部分,正是文学的广阔之境。新闻与文学会彼此滋养,在某些地方互为镜鉴。许多杰出作家从事过新闻工作,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恰是优秀的作家,这正阐明了文学与新闻之间密切的关系。
王淼:您在小说中塑造了杨威、心丽、张石磊、思然等丰富的众生相。这些众生相归根结底指向了什么?是对个体命运的绘制还是对时代发展的追踪?
黄朴: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应该有历史使命感,有思想家的锋芒,敢于质疑、敢于反思。优秀的作家始终是时代精神的先觉者、先行者、发现者。我小说里的众生之相力图指向一个群体的心灵变迁和精神轨迹,小人物的悲欢与哀歌,呈现了人性的幽微与纷繁,浓缩了现实中国的细微变迁,他们是时代前行的缩影。
王淼:您的创作始终聚焦与时代共舞的小人物的命运。如果说小说集《丫丫的城》《新生》是在集中勾勒“星丛”式的小人物众生相的话,那么您的首部长篇小说《如我》则是试图聚焦以思然为代表的进城农村女性的小人物命运。让我好奇的是,您为什么没有承继当代文学对“农民进城”的“少平进城”式的叙述惯性,而是选择以农村出身的女性“思然”之口,以其“如我”的讲述姿态,书写新世纪农民进城的故事?
黄朴:当代文学中农民进城的故事比较集中于书写农村男性青年的奋斗史,“高加林”们的故事我们听得太多了,但农村女性的困境更值得被看见。与男性相比,女性的进城之路更艰辛,她们不仅要对抗物质生存,更要承受性别权力的压迫。我在长篇小说《如我》中,不仅书写了像巧珍一样善良温柔的思然被欺凌、被损害的命运,还突出表现了以她为代表的“巧珍”们与这个男性主导的世界的冲突、对抗和灵魂的自我救赎的过程。
小说标题“如我”二字于是有了新的含义,即跨越时空的疼痛的传递,从一个女性传达到另一个女性。
王淼:与您以往对人物内心“专心致志”地观照不同,您在《如我》中写了不少“狗”“鸟”“鱼”之事。有学者将之称为您精心营构的“动物隐喻体系”。您对此怎么看?“狗”“鸟”“鱼”背后究竟隐喻了什么?您是否打算今后创作“动物小说”,开拓除“人”之外的叙述视角?
黄朴:关照动物是我的叙事策略之一。《如我》中,“狗”象征底层民众的漂泊,“鸟”映射知识分子的压抑,“鱼”隐喻都市青年的异化。这些意象并非刻意设计,而是人物精神世界的自然投射。未来若发现动物能承载人性重量,或许会探索“人兽共生”的寓言体写作。
王淼:很长一段时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成为一种“老生常谈”。随着“中文创意写作”正式入列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这种“老生常谈”再度引发热议。作为一名优秀的作家,您认为写作是一种可培养的、可学习的能力,还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天赐?您尝试过用人工智能DeepSeek创作吗?您觉得人工智能是否会冲击、甚至变革文学的当代流向?
黄朴:文学或其他艺术创造都需要天赋。但后天坚持不懈的努力,确实可以成就一个作家或艺术家。“创意写作”在当下高歌猛进,形成热潮,它对写作者天赋的挖掘、科学的写作训练、综合素质的提升都起到了巨大的催化剂作用。“创意写作”已经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家。
AI或许能生成完美的文字碎片,但永远无法抵达“人性的深处”。文学是生命的体温、灵魂的震颤。就像商洛的茶叶,AI能复制外形,却泡不出秦岭雨雾浸润的甘醇。不过,我愿意尝试与AI合作——让它进行素材整理,而我专注在灵与肉的深处捕捉那些机器永远无法理解的微光。
王淼:近年来,部分读者处于陕西文学“断层危机”的焦灼与不安中。作为陕西文学“承上启下”关键代际的“70后”作家,您对此怎么看?
黄朴:陕西文脉如秦岭般绵延不绝。陈忠实、贾平凹等前辈如同主峰,我们这代人是山间的溪流或者支脉——看似分散,实则汇聚成河成峰。所谓“断层焦虑”,或许是时代对文学过度消费的产物。真正的经典无需喧哗,时间自会证明。
黄朴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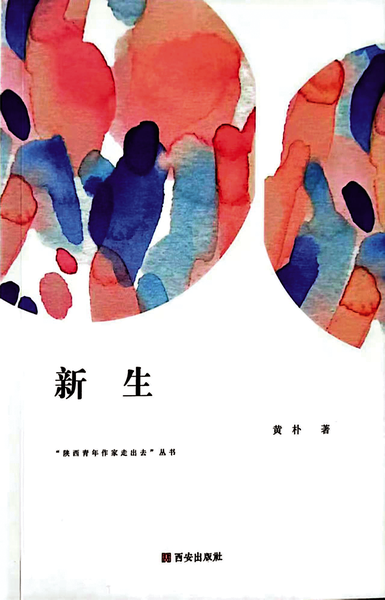
黄朴作品《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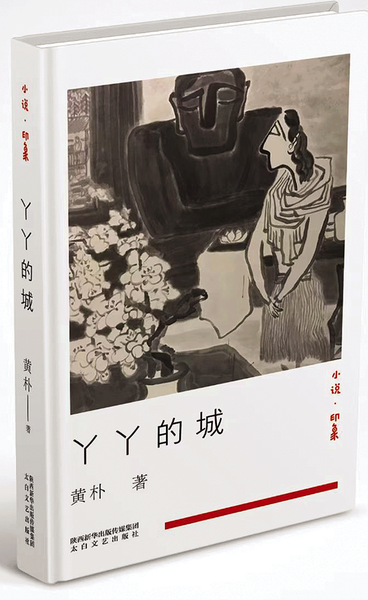
黄朴作品《丫丫的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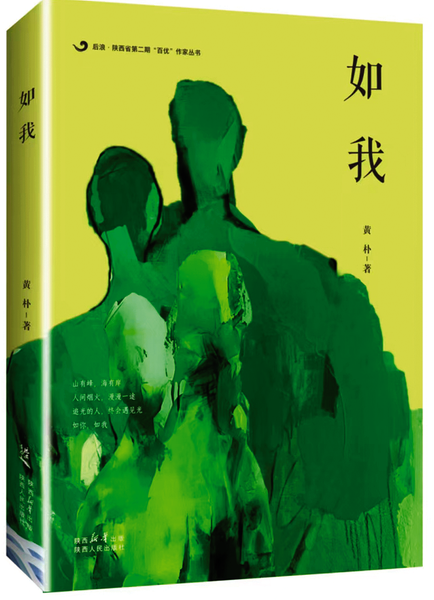
黄朴作品《如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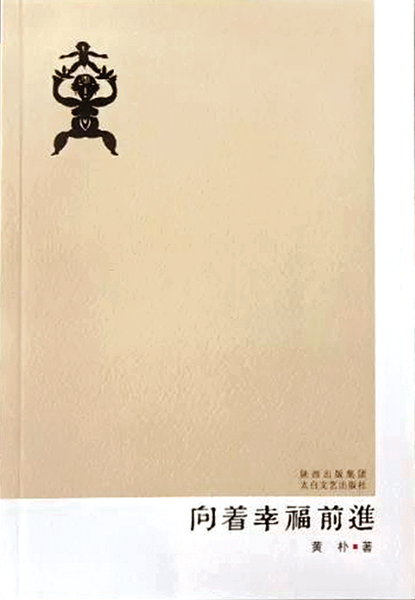
黄朴作品《向着幸福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