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新闻信息许可证服务编号:61120190002
陕西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29-63907152
2025-05-26 09:13:22 来源:王宜振教童诗
学语文,从读童诗开始
“王宜振教童诗”栏目以推荐中国现当代适合儿童阅读的较新的诗歌文本并对之加以品读为主,以此推动全国诗教工作的开展。同时,本平台还开辟“孩子的诗”“诗教课堂”“诗歌后面的故事”“好书推荐”等栏目,欢迎全国诗教工作者、诗人参与互动,共育诗歌教育的花园。

好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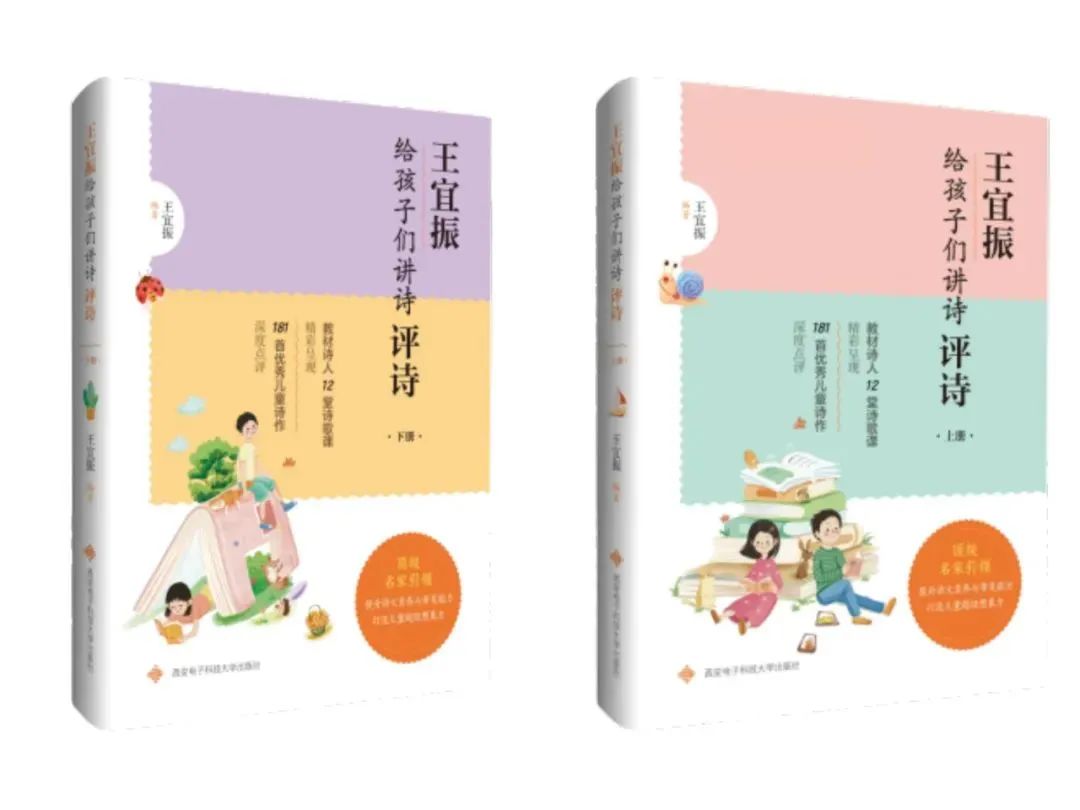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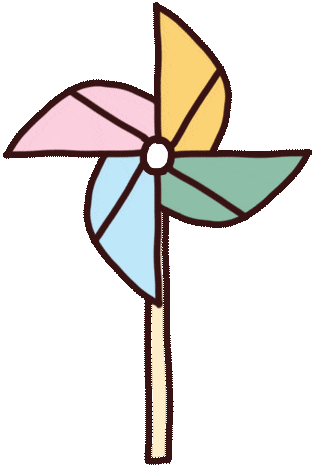

本期推荐

推荐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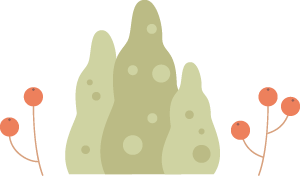
黑女不姓黑,姓郭,本名叫郭艳梅。她长期从事教育,对诗歌教育情有独钟,她还为孩子编写了一套诗教教材,有一些诗教学校在使用。过去,她一直创作成人诗,曾获过北京文艺网诗歌奖,近年来,她又开始写儿童诗。她的童诗具有自己的个性,是对生活的深切体验和感悟。建议大家读读她的诗和诗教文章,我们相信,从中一定会受到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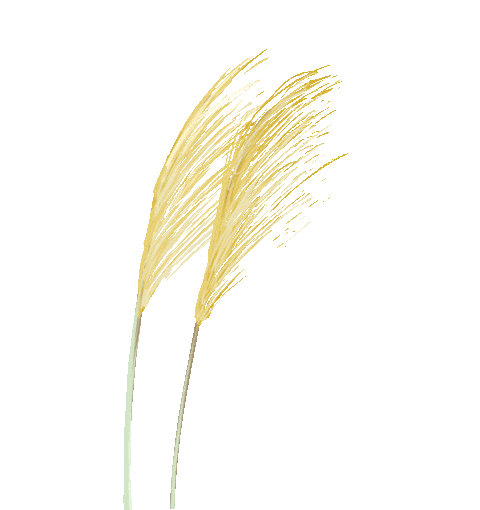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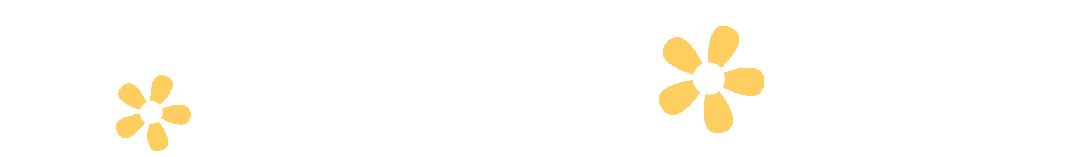
生活的教育(组诗)
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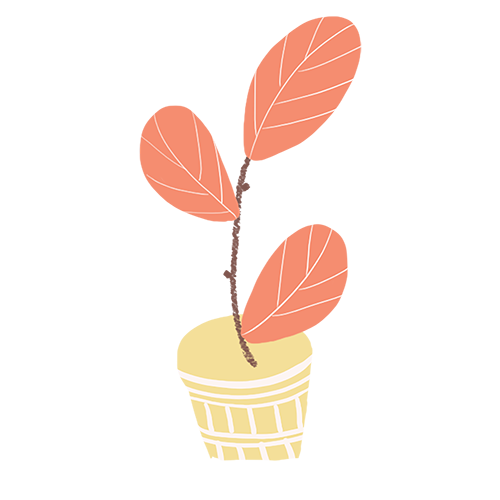
生活的教育
孩子,如果你一定要穿过
那片林地,不要晚上去
草地和鲜花后面,狐狸正编造
下一条谎言
大灰狼在树缝中窥视
萤火虫也许将你引入歧路
摄人灵魂的猫头鹰在搜寻
爱偷窃的鸟儿盯着你
胸前的钮扣……这些都来自
生活的教育,孩子
当然,生活的教育还包括
杮子经霜才能变甜
沿一个方向挖会创造一口井
如果你爱生活,笑就会比哭
多得多……

伞
下雨了,妈妈喊孩子:
“快回来,宝贝!”
“妈妈,我有伞!”
他指着头上的大树。
树上的小鸟听到了:
“我也有伞!”
叶子上的蜗牛听到了:
“我也有!”
“我有”“我有”……
这些声音来自蚂蚁、蝴蝶,
还有树下的草、甲壳虫,
刚落的几颗小果……
大树笑了——它喜欢这些
毛绒绒的声音。

梦种子
一个人掂着钱袋子,
走到孩子最多的地方。
“小朋友,我想买你的梦。”
孩子想了想,害羞地凑到他耳边
说出了自己的梦。
“不行,你的梦像沼泽,
会弄湿我的灵魂。”
又一个孩子走到他跟前,
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梦。
“不行,你的梦像番茄酱,
不合我的胃口。”
不服气的孩子走过来
一个接一个说出自己的梦,
有的一下子说出两个:
一个是梦,一个是梦想。
“不,不行,你的梦太干燥。”
“也不行,你的太呛鼻。”
就这样,他口袋里装满了梦,
却没有付出一毛钱。
孩子们沮丧地走散,
很快就忘了买梦的人,
但曾说出的梦,
像种子落进心田。

做星星的孩子
妈妈,刚才,就在你喊我时
我不能回答,因为正和一颗星星通电话
它会捎信给云朵
说花园里的种子要发芽
(星星说他更喜欢霓虹雨)
而月亮睡着了,打着紫色的呼噜!
……
最后星星对我说:回去吧!
拔掉大人们身上的刺
让他们痛一晚上,才能学会
拥抱孩子……
妈妈你瞧,星星以为我是
仙人掌的孩子,因为我头上插着一朵
仙人掌花
这下你知道了吧,妈妈
如果我不愿意,你就永远
找不到我

花的节日
妈妈,今天有一个节日
就像一个孩子刚刚降生
没有人知道它的名字
妈妈,这个节日不在
规定的时间
也没有指定的内容
它是我们家的
是我们的——
阳台上的第一朵花开了
今年春天的第一片红
妈妈,它对着我们笑
它用细得听不到的声音说:
“亲亲我,我很香。”
妈妈,笑一个
笑一个,你今天就
和它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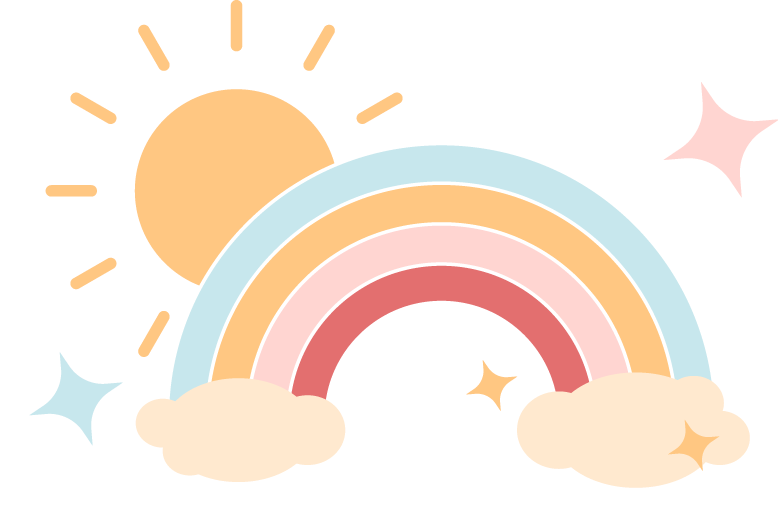
捉迷藏
马车下面,牛圈里,黑墙角
千万别动
越难忍的地方越安全
“出来吧,我看见你了!”
如果你真出来,就中了计
不过这招只能用一次
机灵鬼一个个被揪出来
有的是藏头露尾
有的一紧张就打喷嚏
被找到的站在一起数人
忽然远处传来
妈妈的呼唤
那个藏得太深的孩子
自己走出来:
来找我呀,我就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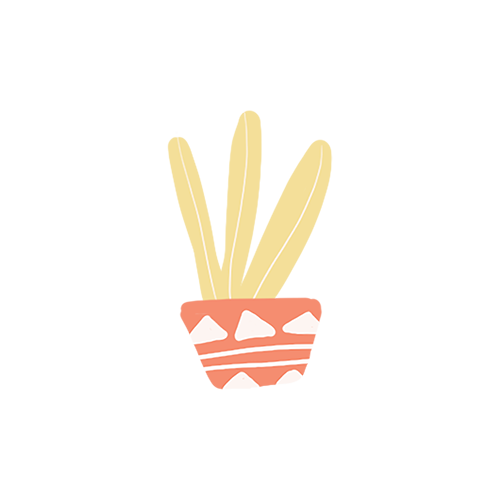
位置
你看,孩子,一切都在寻找
自己的位置——
花香必得散去,种子定会深埋
星星开在夜空,桅子开在枝头
就是这样,孩子,一切事物
美好的样子
都是因为它们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孩子,那些还在路上的事物
不必着急,它们走得慢些
但一定会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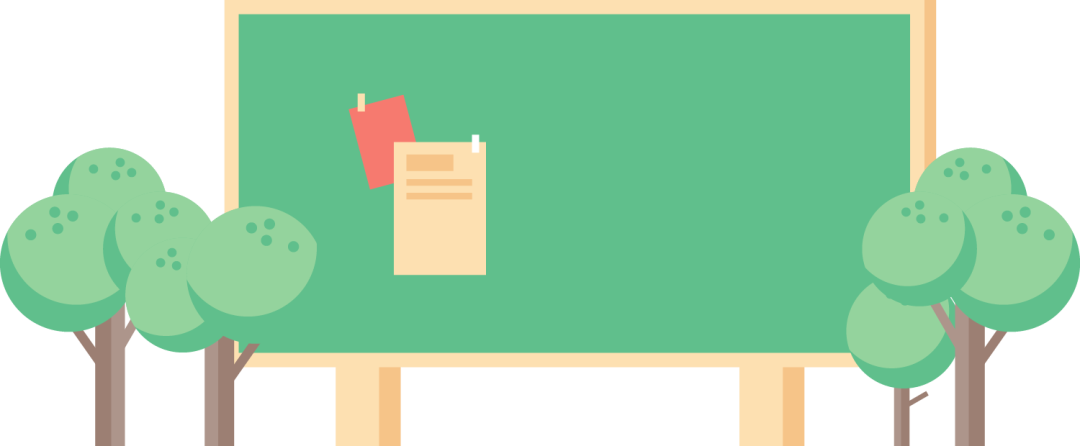
诗的语言之美
——兼谈我为什么做诗教
黑女
诗歌语言的美是多维度、深层次的,它蕴含在音韵、意象、情感以及哲思等多个方面。我在这里谈三个方面:
1.语言的形象美,形成美的意象。
诗,尤其是童诗,总是塑造可感的形象来表达思想和情感。为什么一个精妙的修辞就是一首小诗?为什么可以从修辞手法的运用开始教孩子写诗?因为修辞意味着形象性。形象性使孩子迅速摆脱过于主观的直写,使诗的成功率更高。当这种形象成为某种情境、思想或感情的代言,就成为意象。
这是美国女诗人狄金森的《蜂鸟》:
一条倏然消失的路
有一只飞转的车轮——
一声祖母绿的反响——
一阵胭脂红的奔腾——
灌木上的每朵花
都摆正碰歪了的头——
威尼斯来的邮件,或许
一次清晨骑马闲遛
这首诗意象鲜明,想象奇特,充满生命的惊喜和欢快。全诗运用通感,将声音、色彩、动作打通一气。这种蒙太奇手法使观看这个行为变成魔法。这是诗人的通灵时刻,在她见到这只蜂鸟时,全身心的感受细胞打开了,无尽的联想和想象喷涌出来。这种感受力的巅峰时刻使这只鸟进入了诗人的生命史。人的感受力是需要经常打磨的,而这类诗正是提升我们感受力的载体。再看这首诗:
帆
莱蒙托夫
在那大海上淡蓝色的云雾里,
有一片孤帆在闪耀着白光!
它寻求着什么,在遥远的异地?
它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
波涛在汹涌——海风在呼啸,
桅杆在弓起了腰轧轧作响,
唉,它不是在寻求什么幸福,
也不是逃避幸福而奔向他方!
下面是比蓝天还清澄的碧波,
上面是金黄色的灿烂的阳光,
不安的帆,却在祈求风暴,
仿佛是在风暴中才有宁静!
这首诗分为三节,第一节提出问题,第二节分析问题,第三节回答问题。诗中的两个问号、三个感叹号加重了情感,这情感中有坚定、激昂、豪迈。它的结尾也给人以震撼和深思:风暴中才有宁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宁静?它和大多数人对宁静的理解是如此不同!
帆一般象征着出征,而在这里却是一个不安的寻求者的形象。诗人用帆这个意象表达不满足于安逸和享受,而是要尽可能地去经历或冒险,以探求生活的真谛的思想。这是这首诗的创新之处。
意大利文学家克罗齐说:“没有意象的情感是盲目的情感,没有情感的意象是空洞的意象。”形象才能可感,有情才能动人,诗对学生感受力的培养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2.思之美:给人启迪与智慧
思之美、智慧之美一直是诗的语言之美的重要方面。无论是出于感受还是阅读经验,诗都向我们传达一种非凡的思考。它指向的并不都是对某个问题的解决,更可能是沉思,是发问。诗之思,是通过关系来表现的。这和“美是关系”同理。
我举一个例子,一首诗如果只表达个人情感,那它就可能导致一种宣泄,或者就是呓语。它只有个人性而没有普遍性。相反,如果一首诗只表达普遍情感,那它就可能太普通了,没有个体经验的独特性。所以,写诗,首先要处理的就是个人性与普遍性的关系。
关系意味着对话,因此,诗是人与万物生灵的对话。如果形不成对话关系,那就是自言自语,很难成为诗。诗是内视点艺术,因此它最大的危险正是过于自我。前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这样认为:人类情感的表达、理性的思考乃至任何一种形式的存在都必须以语言或话语的不断沟通为基础,“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对话无处不在,广泛而深入,“……在每一句话、每一个手语 、每一次感受中,都有对话的回响(微型对话)。”钱理群先生在《发现与对话——中小学生写作教育断想》中也提出这种“对话”观:写作是学生与自然的对话、与自我的对话、与社会的对话、与“大师”的对话。
德国新生代思想家韩炳哲认为:中文里的“人”字,指向的不是实体的人,而是表现“之间”的字符,是一种关系。因此, “具备更强的开放性”。
做一位诗人,就是领会世间的真与美,简言之,就得领会善,而所谓善,第一依存于存在与知觉间的关系上,第二依存于知觉与表现间的关系上。
这就像葡萄牙诗人佩索阿写的那样:
我是一个牧羊人。
思想是我的羊群,
我的羊群也是各种感觉。
我思想,用眼睛用耳朵,
用手用脚,
也用鼻子和嘴巴。
……
——《我是一个牧羊人》
思想是感觉,不仅用头脑,也用身体的每个器官。这是一种极致的思。
诗其实不表达哲理,因为哲理是哲学家的事。诗有教育性,但主旨不是教育;诗有哲理性,但主旨不是讲道理。诗不是追求真理,而是表达人和真理之间的关系。诗是感发,感发两个字讲的就是关系。
我们来看两首诗:
鸟和虫子
[美国]希尔弗斯坦 韦苇 译
如果你是鸟,那就得早醒,
早醒的鸟儿捉的虫子多,
睡懒觉的鸟就该活活挨饿。
而如果你是虫子呢,
那么,早醒的虫子
就正好被鸟捉。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大家经常这样说,但从没有考虑过早起的虫子是什么命运,在这个固定格言警句中,人们只站在鸟儿的角度来考量,但是虫子又从尝不是和鸟儿一样的生命呢?
在另一首诗中,有生命的事物和无生命的事物都具有同等的尊严:
鸟儿死去的时候
[俄罗斯]日丹诺夫 刘文飞 译
鸟儿死去的时候,
它身上疲倦的子弹也在哭泣。
那子弹和鸟儿一样,
它唯一的希望也是飞翔。
子弹和鸟儿,一个是伤害者,一个是被伤害者,然而子弹是无辜的,它只是被捕猎者利用而已,因为它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个不能主宰,并非因为它是无生命体,而是因为它是弱者。这就是这首诗非同一般的角度:双重的悲剧。
因此,诗歌语言的思之美不是因为它思,而是它引起了你的思,它启迪、震撼、照亮你,使你对自我、人生、生命产生了新的觉悟,甚至引起了你的创造性的思。臧棣老师有一句话说:“每一首诗都是对泼在语言和灵魂之上的污水的双重清洗。”
诗的思之美还有一种情况:见证和呼吁。这在童诗中并不多,但如果不提出来就缺了一个重要部分。
刽子手…
[俄罗斯]鲍罗杜林
刽子手………
充满了绝望神情的眼睛。
孩子在坑里恳求怜悯:
“叔叔啊,
别埋得太深。
要不妈妈会找不到我们。”
这是二战时期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诗人把它写成诗之后,成为对纳粹反人类罪行的有力控诉。
再比如希克梅特的《死了的小女孩》:
开门吧,是我在敲门
我在敲,每一家的门
你的眼睛看不见我——
因为,谁也看不见死了的人
我死在广岛,
多少年过去了,又要过多少年
我曾经七岁,现在还是七岁——
因为,死了的孩子不会长
火烧毁了我的头发
后来,眼睛也被蒙住了
于是我变成了一小撮灰烬
风,就把灰吹走了
……
诗人用这首诗告诉我们,即使是有罪的国家,也有无辜的百姓。就像无辜的子弹一样,他们同样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这首诗使用第一人称,用孩子的口吻来诉说,更能引起感动、震撼和同情。这两首诗没有一个词是反对战争,但我们在每一句中都能读到这个主题。著名美籍波兰诗人米沃什说有一句话:“诗的见证,比新闻更可靠”。我们的孩子读到这些诗的话,就不会像社会上有的人那样喊叫:打吧,打一仗才过瘾!当然,如果需要反抗侵略,保家卫国,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走上战场。
3. 情感之美:升华精神,涤荡灵魂
一首诗能引起读者的感动并不容易。而被感动也是一种高级的情感,它是同理、同情心的表现,具有升华心灵、纯粹情感、涤荡灵魂的功能。当我们读到一首好诗,你头脑中“嗡”地一声,像是那根粗重的、平时极难被拨动的弦颤动起来。其实好诗大都有这个特征,下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两首貌似平静的诗。
暮 色
[希腊]萨福 水建馥 译
晚星带回了
曙光散布出去的一切
带回了绵羊,带回了山羊
带回了牧童到母亲身边
“晚星带回”,而非月亮,这是一颗最早亮起来的星星。星光指路,这里面有生活的经验。
“带回了”重复了三次,在音韵美之外,这种反复也带给我们一种隐然的感动。“带回了绵羊,带回了山羊”,在重复的声音中稍有变化。如果改成“带回了牛群,带回了羊群”呢?它就太普通了。没有原句的意外之美,孩子气的笨拙天真之美。
“带回了牧童到母亲身边”孩子回家,回到妈妈身边,是什么情景?诗人不再写了,只把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
两个短句,结尾一个长句,体现出语言内部的音乐美。
还有一首诗也是关于“回家”:
钓鱼
柯岩
天黑啦,
天黑啦!
钓鱼的,
回家吧!
你的妈妈
在等你,
鱼儿的妈妈
在等它……
首先,标点符号的使用值得我们细品;其次,第二人称的运用,直接对钓鱼人喊话,表达出孩子救小鱼的急切心情。整首诗是祈使、恳求的感情;第三,情感的含蓄和动人。钓鱼的人是个大人,但孩子用自己的心理来劝说他:你的妈妈在等你……无论什么年龄的人,都会被这句话感动。
这首诗中有真正的天真,而非伪装的天真。它通过孩子对鱼儿的同情表达出一种生命无差等的爱。这种爱的教育其实就是最好的心理健康教育。俄罗斯诗人雪莱说:“诗灵之来,仿佛是一种更神圣的本质渗彻于我们自己的本质中”,读一首好诗,何尝不是这样。
诗的抒情是含蓄的,常常通过一些意象表达出来。越是含蓄,越耐品味,情感也越丰厚。比如罗大里的《移民列车》、王宜振老师的《父亲从乡下来》、金波老师的《雨天,我和一只白色的鸟相遇》等等。
我们常用一比喻来说教育:春雨润物细无声。教育的特征正是这样的:温润、细腻、深入。如果拿一件乐器来打比方,应该是小提琴。而诗教这把小提琴的弓和弦正是美和爱。
一首好诗是对人的整体性的提升,这种提升纯粹到无关悲喜的程度。它就像一个新世界,赋予你活力,使你对生命、生活的审美超越喜怒哀乐的范畴。一首好诗就像一场教育,使我们更人性,更高尚。
当然,如果你把我讲的这些理解成“诗的美”,也是完全可以的。这些浸润心灵的美,不仅有益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也能使他们在快乐中提升各方面素养,这正是我做诗教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