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新闻信息许可证服务编号:61120190002
陕西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29-63907152
2024-02-28 16:16:11 来源:阳光网-阳光报
近日,曹洁长篇纪实文学《生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无定河,古称生水。作者从河流水源地定边白于山走到清涧县高杰村镇河口村(无定河汇入黄河处),走访和纪实无定河流域的自然生态、古堡村镇、传统民居、民间手艺、民俗风情等陕北地方文化,将人与河流、过去与现在、个人际遇与风物景观,交相融汇,物我合一。
陕西人民出版社邀您共同探寻河流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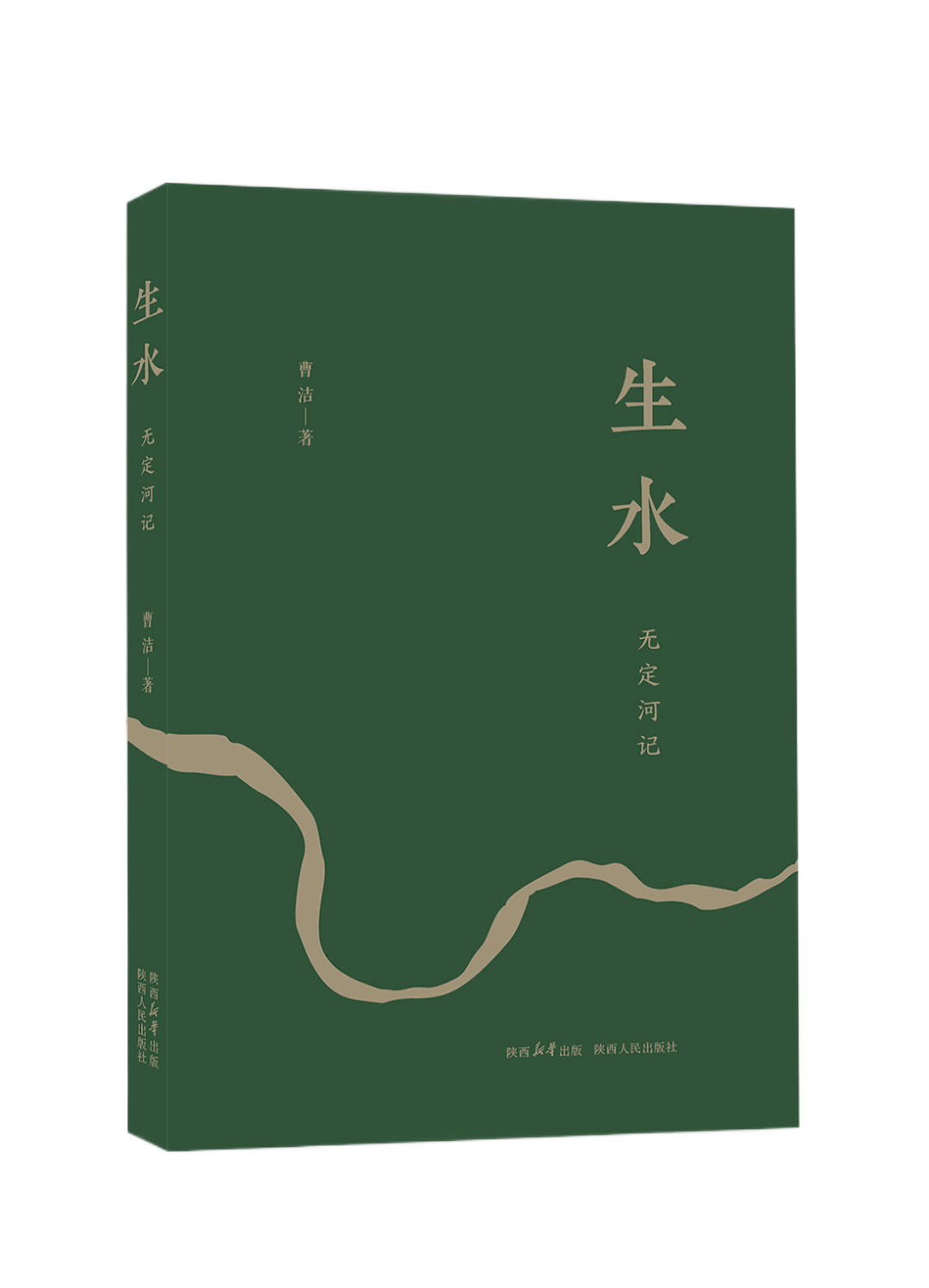
《生水》
作者:曹洁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无定河:河流是生命的艺术品
无定河,古称生水、朔水、奢延水,我愿意喊他“生水”。
生水,这不是陌生的水,而是不断生长的水。唐五代以来,无定河流量不定,深浅不定,清浊无常,就像少年,新奇、叛逆、撒野,但他是阳光的、明朗的、奔腾向前的。向前奔腾的进程中,他将纳林河、海流兔河、榆溪河、芦河、大理河、淮宁河等三百多条大小支流,纳入自己的血脉,不断拓展生长领域,并与多种地域文明,相生相长。
自远古而始,人类逐水而居,繁衍生息,这样的生存模式既是造物主的安排,也是人类的自然选择。人类沿着河道栖息,采集狩猎、钻木取火、打磨石头、烧制陶器,所有与生命相关的生存细节都离不开水,水养育了我们的先祖,也哺育了绚烂的原始文明。同时,不同的河水流向与经纬变化,又形成地理迥异的自然元素,但种种文明要素在时间与地域上的分布并不均匀,从而造就了内涵互异的文明质地。
人类多么幸运,不只承享着河流的无私供养,还创造出特质各异的河流精神与大地文明。远古时期,无定河流域就居住着多种民族,逐渐形成多民族融合的农业社会,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相互惠。不仅在陕北大地上留下丰富灿烂的地域文化,而且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沧海桑田,看不见的时空中,他不停息地汇聚百脉细水,从而走出广阔丰厚的流域文明,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生生不息。对一条河而言,纵向延伸,横向扩展,向人类喻示着永恒的大地伦理和河流美学,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长,而是历史与人文的成长。
哲学上这样定义:文明是历史长久以来沉淀形成的,有益于增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适应和认知、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被绝大多数人认可与接受的人文精神、发明创造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文明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的集合,至少包括家族观念、语言文字、宗教信仰、观念法律、城邦国家等要素。
《易经·乾卦》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阐释:“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似乎最初“文明”指“文采”,可他又阐发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之论。其实“文明”与“野蛮”相对,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广义来讲,文明包含人类所创造的全部文化成果,对引导社会主体价值观念产生着深刻影响,文明的主要要义就是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成就和功绩。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绝不是一个虚设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象:一只采摘种子的女人之手,一颗被男人磨光的石球,一把石刀或石斧,乃至甲骨片上刻着的象形文字。正是这些有形之物,使人类这种智慧生物走出蛮荒,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大地,将文明之根深扎土壤,谱写了人类耕耘大地的智慧史诗。
无定河流域文明是一种极具地标性的区域文明。数千年来,陕北走过原始农业时期、传统农业时期、近现代农业时期,不同地域和流域又产生了不同的农业类型,并随之形成互异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作为黄河一级支流,陕北高原的母亲河,无定河不只孕育了丰富灿烂的地域文明,也有力地证明了陕北人从何处来,往何处去。
陕北高原突起在辽阔北方,白于山又高出北方高原之上,成为繁衍生命的水源地。《山海经》记:“上多松柏,下多栎檀,其兽多㸲牛、羬羊,其鸟多鸮。洛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渭;夹水出于其阴,东流注于生水。”羬,是古代汉族传说中的一种野兽,形状像羊,却长着马的尾巴;鸮,亦称猫头鹰,一种凶猛的鸟。这段文字中潜藏着一股澎湃水流,就涌动在白于山。远古时期的白于山,高山与大河相依,原野与涧地相生,森林茂盛,猛兽栖居,松涛阵阵,鸟雀欢鸣。
2017年7月24日,陕北七月,晴天浩瀚,阳光绚烂,紧跟着白云的脚步,我们深入白于山腹地。站在高山之巅,群峦起伏,沟壑纵深,塬隆成了梁,梁变成了峁,峁削成了沟,沟纵深成壑。传说中的松柏、栎檀、牛羊、猛禽以及丰美水草和旖旎风光,都不见了,它们像走失已久的孩子,散落在大山的褶皱里,似乎再也追寻不得。
一种空荡荡的感觉浮上来,又被连绵大山轻轻压下去。
陕北子民的水塔——白于山,他的深处严重缺水,一些村庄已不适宜人居住,但没有谁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年轻人进城打工,老人们宁愿守着一口苦涩的雨水窖,守住无可替代的家园。时代赋予一些新的生活方式,他们骨子里却依然守着原始的个体命运与悲欢,并在蜕变中守着如初的生命常态。
山川亘古,万物自尊,很多年过去了,白于山依然是一座代表陕北高地的父性之山,雄浑大气,威武自重,横贯东西八百里。他健长而有力的臂膀,将定边、靖边、横山南部及吴起、志丹、安塞接壤地区等地,统揽在怀;他敞开胸膛,护佑着山中灵物,滋生了延河、北洛河、无定河等数脉河流。在白于山,我是一个贸然闯入的过客,说不出一个属于大山的名字。魏梁、郝山、马鞍山、花凤子梁、张元峁梁,这些陌生的词语,一个个迎风扑面而来,我却恍然不识。
我能够说出口的,只是儿时所知的一条河——无定河。
这条大河就发源于白于山。他从大山底部开始走,携带着泥沙,一路奔涌向前,翻滚着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融合中奔腾的浪花与沉潜的流沙。秦汉之际,无定河流域森林茂密,水草丰盛,牛马衔尾,自然景观碧水青山,农牧林业兴旺发达。后来,历代战乱连绵不断,屯军开垦,毁灭森林,破坏植被,两岸的地形地貌也发生了很大变迁,逐渐形成了风沙滩地、山塬涧地、黄土丘陵沟壑三种类型,呈现出一派荒凉。到了唐代,河水不再是清流,“无定河”之名始见于唐代中叶。宋代,著名军事家、科学家沈括曾在陕北一带率兵抗击西夏,对无定河流域做过详细考察。《梦溪笔谈》记:“余尝过无定河,度活沙,人马履之,百步外皆动,澒澒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处虽甚坚,若遇其一陷,则人马拖车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孑遗者。”真实生动地描写出无定河泥沙滚滚飘忽不定之情状。
我们从无定河的下游来,逆流而上,只为奔向他的源头。我们惊喜地发现,看似纵横干涸的沟壑中,每一条山沟里都有清冽的细水渗出,滴水聚汇,汇成一条小溪,蹒跚起步,逶迤而去。漫漫长路,河水由西北向东南(经乌审旗无定河镇巴图湾转向东流,过镇川堡后又折向东南),流经定边、吴起、靖边、鄂托克前旗、乌审旗、横山、榆阳、米脂、绥德,最终在清涧河口注入黄河。
有人说,无定河流经路线形似马蹄,向北凸出,这种不自然的转弯与构造运动有关。在我看来,无定河流经区域更像一片树叶,一条叶柄,支持着数条叶脉,经络分明,汩汩而动。不管江海横流还是日转星移,他总是专注地流向黄河,完成一程漫长而艰辛的生命归宿。
河流是造物主的艺术品,河流也是生命的艺术品,艺术品是唯一的,产品只具备流水线性。一幅山水之美不在题材定位,而在于心性意趣的渗透,远近浓淡、知白守黑、虚实相生、动静相宜,所有细节都是作画者性灵触须的深入,心至意达;无定河的源远流长也不在于源头细微,而在于沿途的伸展、包容和吸纳,滴水聚溪,大水成河,抽刀也断不了。
走在无定河畔,我一直在想,无定河之所以源远流长,那定是缘于人水相依,天人合一。孙中山先生《国民应以人格救国》一文中说:“古人所谓天人一体,依进化的道理推测起来,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成,既成人形,当从人形更进化而入于神圣。是故欲造成人格,必当消灭兽性,发生神性,那么才算是人类进步到了极点。”也有人说,维持和繁衍生命是人的动物性,寻求生命的意义则是人的神性。人终究不是神,人却能沐浴神性的光泽,逐渐远离动物性,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当我的舌尖儿紧咬着“无定河”这个名字,远涉、探寻与走访,抑或朝圣,大概就是想看看天地,看看众生,也真真切切看看自己。
是的,看看就好,一个人究竟能不能在天地之间看见众生,或者在众生中看见自己,似乎不是唯一目的。我只愿在这个行进过程中,沿着无定河的蜿蜒流向,以脚步丈量的方式,走过他走过的村庄,见过他喂养过的子民,看过他滋生的草地和树木,叩问一条河的生命神性。多年后,我依然会清晰地怀想:阳光绚烂,纤细的水草摇曳清风中,一道白于山水门向我们轻轻开启。那是河水之门,也是生命之门,从这扇门走到另一扇门,我找到一个又一个水分充盈的自己。
2017年8月1日 榆林
作者简介

曹洁,笔名如水,陕西清涧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素履》《别院》《采薇》等,作品刊发于《文艺报》《散文百家》《延河》《朔方》等报刊,多篇作品收录于《2014中国散文年选》《2016中国散文排行榜》等文本。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